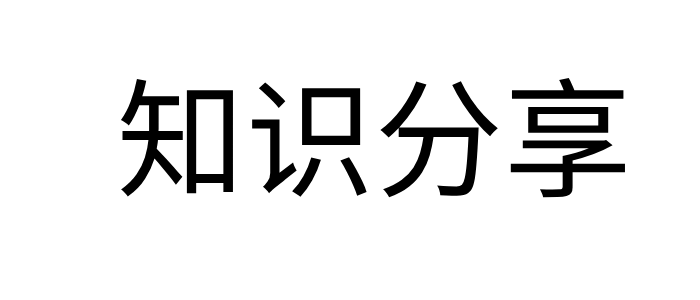作者:王晓辉
清宫剧里经常有达官贵人吸入鼻烟的镜头:从手指上的精致鼻烟壶里倒一点点出来,送到鼻孔里,轻轻吸入,然后闭上眼睛,大声打喷嚏。虽然在别人看来不雅,但吸鼻烟的人一定觉得很舒服。
鼻烟是用上等烟叶混合薄荷、冰片等药材,磨成粉末,密封陈酿数年而成。具有提神醒脑、解郁开窍的功效。据说明朝万历九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携带的贡品中,除了钟和地图,还有鼻烟。鼻烟最初传入中国时,被称为“Snnahu”、“Snnahu”或“西拉”。Snnahu和Snnahu是英语鼻烟的音译,字典解释说这是一种粉状烟草,人们通过鼻子快速吸入。雍正时期,雍正帝觉得既然鼻烟是用鼻子闻的,直接叫“鼻烟”不是更好吗?于是,进口产品“鼻烟”有了一个中文名字——鼻烟。
早期鼻烟是舶来品,价格昂贵。起初只是达官贵人学者的一种优雅。后来随着鼻烟的广泛流行,成为一种社交方式。鼻烟可以用来招待朋友,表达友谊和尊重。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聊天,啜饮鼻烟。喷嚏声此起彼伏,同时令人捧腹。这种聚在一起打喷嚏的方式,比起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集势,差了一千多里!
鼻烟的熏制方法虽然不是很考究,但是它的药用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可以提神醒脑,启迪心智,增长智慧。到了清朝中后期,鼻烟已经成为大户人家的常规之物,到了清末民初更加普遍和时尚。梁实秋老师在他的散文《雅舍小品》里说,他爷爷虽然不抽鼻烟,但是他有十三太保。12个小瓶子围着一个大瓶子,瓶口用棕褐色的布紧紧裹着。每一瓶都有不同的味道,它被放在一个盘子里,呈现给客人。
现在几乎没有吸鼻烟的人了,但鼻烟壶依然作为一种文学玩法,备受收藏者追捧。中国人比欧洲人更高雅,鼻烟壶用玉石、祖母绿、玛瑙、水晶制成,做工精致,造型各异。还有一种水晶彩绘的鼻烟壶,在透明的瓶中绘有山水人物。它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精致。
 资料图:瓶内彩绘玻璃鼻烟壶。视觉中国
资料图:瓶内彩绘玻璃鼻烟壶。视觉中国
《红楼梦》中也有鼻烟的描述。五十二回,晴雯病了。虽然她吃了药,但没有效果。她仍然发烧、头痛和鼻塞。宝玉命麝月去取鼻烟:“你闻一闻,几口就好了。”麝月便去取了一个镶双金星玻璃的金扁盒来,递与宝玉。宝玉掀开盒盖。里面有一个黄头发、西珐琅的裸女,两边长着肉肉的翅膀。它含有一些真正上等的王茶外国烟。晴雯只看了看图,宝玉道:“闻闻看,上火就不好了。”晴雯听说,用指甲挑了一些,吸进鼻子里。为什么,然后我又挑了一些。突然感觉鼻子里一阵酸辣感,渗透到囟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喷嚏,眼泪鼻涕齐刷刷地流。晴雯连忙收下盒子,笑道:“太好了,辣!”……宝玉笑道:“怎么样?”晴雯笑道:“真是快了。只是太阳还是会痛。”
这个描述虽然是生活琐事,但是包含了很多有趣的信息。在曹雪芹的时代,鼻烟深受上流社会的追捧,常用来缓解头痛鼻塞。晴雯用了,觉得有效果。当时最好的鼻烟是进口的。以曹当时的社会地位,曹雪芹应该对这些奢侈品很熟悉。这一点从他对鼻烟壶的细致描写和晴雯对鼻烟吸入的感受就可以看出来。贾宝玉赠晴雯“上等王茶洋烟”,芝罘斋有注:“王茶,西方上等珍烟。”可见“王茶”应该是西方鼻烟的著名品牌,类似于今天的万宝路
 这样一段有声有色的描写,高手是怎么翻译的呢?我们来看看霍克斯教授的译文:
这样一段有声有色的描写,高手是怎么翻译的呢?我们来看看霍克斯教授的译文:
宝玉道:\”把鼻烟拿来。\”。如果闻闻它能让她打几个喷嚏,它会让她头脑清醒。
马斯克去执行他的命令,不一会儿就带回来一个椭圆形的小盒子,是用砂金石做的,镶有金边。宝玉接过来,打开一看。在西大洋搪瓷的盖子里面,是一幅裸体的、长着肉翅膀的黄头发女孩的画像。盒子里装的是质量最好的鼻烟,外国人称之为安西娅。
\”闻闻看,\”他对晴雯说,天空明亮接过盒子,着迷地看着里面的照片。如果你有我
t open too long, it will lose its fragrance and then it won\’t be so good.\’
Skybright took a little of the snuff with her finger-nail and sniffed it up her nose. Nothing happened, so she scooped up a really large amount and sniffed again. A tingling sensation passed through the root of her nose, right up inside her cranium and she began to sneeze: four, five, six times in succession. Immediately her eyes and nose began to stream. She shut the box hurriedly with a laugh.
\’Goodness, how it burns!\’
\’How was it?\’ said Bao-yu.
\’Much clearer,\’ she said. \’But I still have this headache in the front of my head.\’
曹雪芹不吝笔墨,细致入微;霍克斯忠实原文,一字不漏,可谓佳作佳译。这种非常生活化的描写和对话,写得精彩和译得传神都不容易。对照了杨宪益先生的译本,除了几个词汇,如“西洋”和“通快”的译法略有差别之外,其它基本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对于“汪恰洋烟”一词,杨宪益先生采用了音译的方法,译作“Wangchia foreign snuff”, 而霍克斯教授则用了一个从句,“The box contained snuff of the very highest quality, which foreigners call uncia. ” uncia是拉丁语,有好几个不同的解释,既是古罗马的铜质钱币,也是古罗马的计量单位, 还是中亚山区的一种雪豹。我猜测,霍克斯教授选用uncia这个词,可能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uncia的发音与原文的“汪恰”十分接近,甚至说是音译亦无不可;二是uncia是古罗马的一个词汇,在中国一直有鼻烟是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首次传入中国的说法,所以,用与利玛窦家乡有关的一个词汇显得更加靠谱,而且,从发音的角度上说,也会让外国读者感到更加熟悉亲切。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霍克斯教授真的下了考据的功夫,从文献上找到当时确实有一种uncia 牌的鼻烟。
不少红学爱好者也在关注“汪恰”一词的来历,有人认为当时美国弗吉尼亚盛产烟草和鼻烟,“汪恰”应该是弗吉尼亚(Virginia)的音译;还有人考证出十八世纪经营鼻烟的商号中,有一家名叫Maximilian Vachette,据此判断“汪恰”就是Vachette的音译,来自西洋商人的姓氏。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汪恰”这两个字,就当是曹雪芹先生留给我们的字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