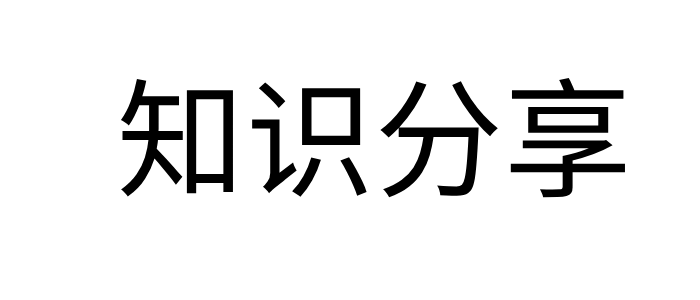800多年前,朱在他的诗《精舍》中写道:“客居深山四十年。”这里的“山中”指的是武夷山,“舒勤”象征着在山中生活,包括写作、讲学、授徒、交友等朋友中有陆游、辛弃疾等宋代文化名人。
冲关金晶(易/摄)
朱、陆游、辛弃疾曾多次执掌武夷山重游观(朱两次,陆游四次,辛弃疾四次)。他们被当地人称为“三翁”(朱晖翁、陆放翁、新漂翁)。他们是作家、茶爱好者和美食家。他们三人在武夷山留下了千古佳话,他们在这里相遇相知,畅谈儒道,报效国家和人民。
朱自画像。朱(1130-1200),字惠,号钟惠,是惠安人。后来叫惠翁,又叫朱文公。原籍江南东路(今江西婺源)徽州府婺源县,生于南涧府尤溪(今福建尤溪县)。朱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武夷山融媒体中心/供图)
寄情山水 笔承春秋
惜春十年(1183年),53岁的朱选择在武夷山九曲溪边的隐屏峰下修建武夷精舍。蜿蜒的水中有一座石岛。“巨石高耸,可坐八九人。它被深水包围着,里面的灰浆像火炉一样自然”(朱《武夷精舍杂咏诗序》)。朱把这块巨石命名为“茶厨”。
除了写书讲学,朱还经常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或弟子在九曲溪畔漫步,爬上五块巨石,留下无数鲜活的故事。清代董天公《武夷山志》诗《试茶,寻仙厨,诗夜尚年轻》写于《茶灶》,描绘了朱等人爬石煮茶,赏景作诗,半夜仍流连忘返的情景。
早市(吴新正摄)
我们来看看朱的《茶灶》:“仙翁留石炉于水中央。饮柜,茶烟香。”
茶炉书法拓片。(钟/供图)
《茶灶》全诗不拘泥于文人沏茶汲水、寻茶赋诗的一般场景,而是随意讲述古代神仙的故事,让五歌水中的茶炉石笼罩在神秘之中。
后来,朱请了一位石匠在五块巨石上刻上“茶炉”二字。南向石雕,宽60150厘米,每字5040厘米,距水面120厘米。
朱《茶灶》受到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追捧,如杨万里、袁殊、陈梦庚、蔡廷秀、董天弓等人,都曾唱过响应。如朱的好友、南宋文学家、诗人杨万里称赞:“茶炉作,飞摘茶乡。在武夷山,溪心化为石。”把茶炉石比作武夷武曲的心脏。另一个好朋友,南宋史家袁树士云说:“采茶,棚仙岩,汲水潜洞。然而旋转石在灶上,轻覆欧州雪。清风在腋下,清香还在舌尖。你什么时候在孤独的船上?来这里分享剩下的。”表达了对武夷山水和茶的怀念。
陆游(1125-1210),殷珊越州(今绍兴)人,汉族,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武夷山融媒体中心/供图)
陆游、辛弃疾没有读过标题为33,360,010-30,000的诗,但也有不少涉及武夷茶的品茶诗。陆游有33,360,010-30,000首诗说“我一生什么都抹了,还带个笔床茶炉”,有33,360,010-30,000首赞“我的舌头下半辈子要一直甜下去。”辛弃疾写了33,360,010-30,000字“酒后清风生两腋窝,齿颊留香”。在寻常百姓家喝茶是家常便饭,但在古代文人的著述中却充满了情趣。
010-695
朱、陆游、辛弃疾等文化经常相继在茶炉石上相遇。沏茶品茶,谈儒谈道,吟诗作赋,留下了许多广为流传的优秀诗篇。
惜春五年(1178年),陆游在建安(建瓯市)推行福建茶盐事业。这时,朱升任崇佑官,二人相聚武夷山。离别多年,陆游写了四首诗,《茶灶》,回忆在武夷山的日子,留下“山少三十六树,水似九折。”“闲来好觉山,静来知日月长”等诗句。
《闲游》记载辛弃疾与朱同游九曲溪,辛弃疾写道《喜得建茶》:“山中有客帝,每日吟诗坐落矶。”“试向精舍老师请教,设在苍溪八卦前。”
muhao.com/pic/img.php?k=福建日报电子报刊平台,福建日报电子版今日在线阅读7.jpg\”>
武夷山天游峰俯瞰五曲行筏 (朱燕涛/摄)
这些诗句展露了“三翁”寄情山水间、心游尘世外的心境,记录了他们寻芳武夷、问道武夷的足迹。
武夷山水是最常见的吟咏主题。令人称奇的是,“三翁”都围绕幔亭胜景留下不少佳作。
冲佑观在幔亭峰下,朱熹《九曲棹歌》开篇写闽越时期的幔亭招宴:“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能让朱熹如此高看一等,可见幔亭神仙会的分量。据《武夷山志》记载,这是古代武夷山祭祀神仙武夷君的盛会,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举行。

幔亭(彭善安/摄)
陆游《游武夷山》中的“少读封禅书,始知武夷君”和《初入武夷》的“未到名山梦已新,千峰拨地玉嶙峋。幔亭一夜风吹雨,似与游人洗俗尘。”都是记述他游览幔亭、追寻仙踪的诗句。
朱熹和辛弃疾同游九曲溪,辛弃疾诗歌《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中也有幔亭峰内容:“山上风吹笙鹤声,山前人望翠云屏。蓬莱枉觅瑶池路,不道人间有幔亭。”
他们笔下仙凡同乐的故事,成为描画武夷人间仙境的经典之作。

武夷精舍(吴心正/摄)
以民为本 志同道合
朱熹、陆游、辛弃疾有时虽不在一处,但联系密切、政见相合、惺惺相惜,不仅都有儒家济苍生、安天下的民本思想,而且均为坚定的“抗金”主战派。

五夫兴贤书院(吴心正/摄)
早在乾道四年(1168年),闽北多地发生灾情,朱熹就劝豪绅发放存粟,以平价赈济灾民,仿效古时做法办社仓。三年后他在武夷山五夫镇建成广受赞誉的“五夫社仓”。社仓侧方有一口与地面平行的四方井,当时为防火之用,被称为“赈灾井”“民心井”。这是朱熹民本思想的重要见证。

朱子社仓 吴心正/摄
淳熙七年(1180年),辛弃疾任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江西各地因旱灾饥荒严重。辛弃疾仿效朱熹做法,向当地豪绅借余粮、筹资金,并千方百计从外地买粮。《宋史·辛弃疾传》还记载,辛弃疾发榜通告:“闭粜者配,强粜者斩。”严禁囤积粮食、哄抬物价,违反者实行发配甚至问斩。这些措施很快收效,当地受灾百姓平安度过饥荒。
此时,朱熹也在江西做官,管辖之地永修、都昌旱灾严重。辛弃疾闻讯,将官府和商人借粮调剂部分运去,解了朱熹燃眉之急。朱熹立即开设粥厂,救济大批灾民。灾情一过,又兴修水利,建立社仓。
而同一时期也在江西为官的“三翁”之一陆游,却因开仓放粮,奏请朝廷赈灾,获“擅权”罪名,被罢官职回到浙江老家。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被推荐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正值浙东发生灾荒,朱熹通过各种渠道征集赈粜米粮,救济灾民,奏劾救灾不力及不法官员,得罪了一些士大夫。陆游闻悉后,特地赠诗一首《寄朱元晦提举》,“劝分无积粟,告籴未通流”“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对灾民饥苦和官府无能的绝望之情溢于言表,声援朱子,支持赈灾。

朱子社仓(小玲/供图)
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期间,赈济灾民、弹劾贪官所取得的成果显著,得孝宗皇帝褒奖,他的社仓赈灾办法缓解了灾情,使饥民无断饮之忧。随后,朝廷将朱熹呈请的《社仓法》,“颁诏行于诸州各府”,广惠天下百姓。

建宁府五夫社仓记(小玲/供图)
在“抗金”大业面前,朱熹、陆游、辛弃疾等三人既有文臣的苦谏,又有武将精忠报国的英勇豪迈。陆游40多岁时穿上戎装,亲赴前线征战。辛弃疾更是几番沙场杀戮,“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朱熹评价他“是一帅才”。
但辛弃疾这样的帅才却屡遭朝廷主和派排挤、打击,贬至武夷山冲佑观担任赋闲的提举,失去“英雄用武之地”。朱熹对辛弃疾遭遇的不公待遇十分不解:“但当明赏罚而用耳!”陆游也鸣不平:“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
这些“抗金”主战派人士壮志难酬。武夷山下,他们“梦里挑灯看剑”,在“茶灶石”前空留壮怀激烈的前情往事令人感怀。
所不朽者 垂万世名
一生多忧患、坎坷的“武夷三翁”,武夷精舍时光是难忘的,三人的知遇也最为难得。

武夷山摩崖石刻(吴心正/摄)
晚年朱熹陷“庆元党禁”,处境艰难。声名黯淡之际,许多见风使舵者与朱熹断绝关系,有的门生甚至投靠他人。
但陆游、辛弃疾与朱熹始终惺惺相惜,保持深厚的友情。
辛弃疾写信慰问朱熹,朱熹回信中以“克己复礼”相勉。冬天朱熹寄茶饼、纸被给陆游。陆游写诗“木枕藜床席见经,卧看飘雪入窗棂”暗示抵御严寒的心情。特别是朱熹去世,朝廷明令不得纪念时,是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位文坛泰斗挺身而出,他们的悼友表现和悼亡祭文,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
陆游寄出悼文:“捐百世起九原之思,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忘,庶其歆飨!”
辛弃疾哭于灵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然犹生。”在朱熹生前,辛弃疾的《寿朱晦翁》即作出评价:“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评价之高和认知之深,当时无人可及,在朱熹名声大噪之前可谓振聋发聩。

武夷宫秋色。(陈美中/摄)
武夷山水间,朱熹、陆游、辛弃疾三人的相遇相知,像“茶灶”的仙翁遗事一样,值得永久回味、永久传诵。
(出品:“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新福建客户端)
参考文献
《宋史·朱熹传》《宋史·陆游传》《宋史·辛弃疾传》
董天工(清),《武夷山志》
萧天喜,《武夷山文化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