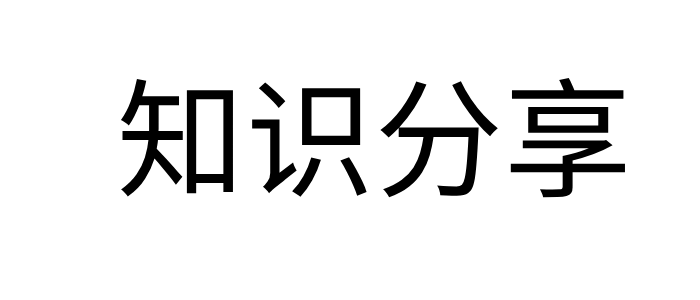由于导言中缺乏准确的统计资料,要知道17、18世纪的居民人数要比19世纪困难得多。此外,帝国由无数领地和大小不一的帝国城市组成的复杂情况,使得这项任务比计算当时像法国这样相对集中的国家的人口数量更加复杂和麻烦。因此,相关的原始数据和统计手册多为粗略估计。
比如柏林著名的地理学家安东弗里德里希毕兴(AntonFriedrichBishing)认为,1801年出版的1789年时,除西里西亚以外的整个德意志人口在2400万至2600万之间.莫里茨戈特利布雷赫曼的《历史统计手册》中写道,1795年的包括西里西亚在内,帝国的总人口是2940万人.在帝国首相的档案中有一份详细的原始数据,记载了十个帝国集团和波希米亚的总人口为25473678人;包括帝国骑士团和西里西亚率领的约25万人。
神圣罗马帝国地图
如果加上居住在这个庞大公国的177.6万人,那么帝国的人口应该是27499678人。大部分人口,即23,360,318人或84.9%,居住在世俗总督的领地(包括西里西亚),3,121,000人或11.3%居住在教会领地,768,360人或2.8%居住在帝国城市。
例如,人口的分布在不同的帝国集团中差别很大。,的库尔勒因集团有762 500人,即75.8%的人居住在教会执政官管辖的地区,只有24.2%的人居住在世俗执政官管辖的地区;还有同时期的勃艮第集团和上萨克森集团却没有教会诸侯的臣民。
维尔茨堡主教宫
生活在教会领地上的居民比例较高的是法兰肯集团,占45%,下莱茵-威斯特法伦集团占36.7%。帝都居民比例最高的是施瓦本集团,占16.3%,其次是弗兰肯集团,占8%。根据帝国议会文件提供的资料,当时各帝国集团的人口数字如下:勃艮第集团,约200万人,下莱茵-威斯特法伦集团,2496870人。下萨克森州员工209.55万人,上萨克森州员工383.087万人,库尔莱茵州员工101.85万人,上莱茵州员工144.71万人,施瓦本州员工162.2738万人,奥地利员工450万人,巴伐利亚州员工150.95万人。总而言之,神圣罗马帝国总计约有2750万居民,而他们分别信仰不同的宗教.
当时,在西班牙和法国,天主教是国教,而在英国、丹麦和瑞典,国教是新教。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规定,在上述这些国家里,属于少数教派的人,或是受到歧视或是不被容忍。但是,在神圣罗马帝国里却存在着多种宗教或教派。,的天主教、路德教和改革派(加尔文教)三个教派都是合法的,并得到教廷的完全承认。此外,在许多领地邦国和帝国城市里,生活着犹太教信徒。最后,还有数量较少的新教信徒,如门诺派、赫琳胡斯兄弟会、佛多教派(13世纪初兴起于法国,主张《圣经》为最高权威,反对弥撒和教皇制度)和胡格诺派(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
英国圣公会教堂内部
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结束了以宗教冲突为起因的残酷的“三十年战争”,保障了三大主要教派之间的地位均衡.这个和约作为一个重要的基本法,对1648年到1806年的帝国法律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以后不可能爆发宗教战争,因为它给帝国和领土层面的教派带来了持久的和解。天主教、路德教派和改革派从1648年起处于平等的地位,它们的地位受到法律的保护。
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前。
然而,对少数犹太人(占帝国人口的1%)、门诺派、波希米亚兄弟会和其他一些教派的宽容或不宽容的态度因其所在的国家和城市而异——虽然这些少数派从未受到过完全平等的对待,但至少在许多地方,是允许他们在公众场所做礼拜的。,的一个犹太中心尤其如此,它在班贝克父系修道院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犹太社区,该修道院建有许多犹太会堂,甚至还有一所犹太塔木德大学。
欧洲犹太人的老照片
18世纪末,约58%的天主教徒、41%的新教徒和1%的犹太教徒生活在帝国内。如果你看看各个帝国集团的教派分布
,就会发现像约翰雅各布莫泽尔所说的那种状况,有的全部接受新教信仰,有的全部是天主教徒,也有多教派混合的。根据毕兴的调查,上萨克森集团和下萨克森集团是新教地区,奥地利集团和勃艮第集团信奉天主教,其他帝国集团里是多教混杂。可以粗略地说,帝国的北部是新教区域,西部和东南部是天主教地区,其他地方一般是多教派混合。
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教派分裂的结构,就会得到一个完整的图像。检视这个结构,会发现上萨克森帝国集团99.6%的人口是新教信徒,下萨克森有98.5%。也就是说,在1795年,在德意志的北部地区生活着5883000名新教教徒。与此相对,帝国的东南部(哈布斯堡本土,不包括属于普鲁士的西里西亚)92.1%是天主教徒,在那里7575000名天主教徒对约610 000名新教教徒。拥有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徒是有着200万人口的勃艮第集团,巴伐利亚集团的天主教徒达97.6%,而库尔莱茵集团的情况是78.8%的人是天主教徒。
 ▲巴伐利亚慕尼黑王宫内景
▲巴伐利亚慕尼黑王宫内景
与此相反,法兰肯集团(43%天主教徒,56%新教教徒,1%的犹太人)和士瓦本集团(46.3%天主教徒,约53.6%新教信徒)的教派结构比较均衡。在下莱茵-威斯特法伦集团,天主教徒占57.6%,比例较高,但在上莱茵比例要小得多,只占25.2%,那里的新教教徒几乎超过了四分之三。
由于在帝国议会的选帝侯议团中天主教徒占了多数,所以与俾斯麦所创立的第二帝国强调新教信仰的皇权相反,古老帝国的皇权是天主教的。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排除新教信徒成为国家首脑,也有人策划过这方面的方案和行动,但正如海杜赫哈特所揭示的那样,并没有出现过真的要取代天主教皇权的尝试。在这古老的帝国内,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中的许多条款保障着帝国境内教派之间的平等地位,尽管如此,有天主教的皇帝、天主教徒占多数的选帝侯和担任帝国大首相的美因茨大主教,在帝国的法权秩序中,天主教肯定会取得优势。
 ▲位于阿沙芬堡的约翰尼斯堡宫殿,美因茨大主教行宫
▲位于阿沙芬堡的约翰尼斯堡宫殿,美因茨大主教行宫
这虽然也与帝国居民们的宗教信仰比例相吻合,但在新教方面,常抱怨天主教徒受到太多的优待。在某些方面,比如在等级提升和帝国最高皇家法院的某些判决中,肯定存在着这类情况。不过,在那些最重要的共同机构中,如在帝国议会,在所有涉及宗教的重大问题上,是不可以以多数票胜过新教教徒的,这一点得到充分的保障。
在帝国,除了有着信仰的多样性之外,还存在着语言的多样性,它们都是允许存在的。
语言多样性
多样性的语言,对文化的繁荣――即使只是大众文化也是同样是有益的。德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帝国内的大多数居民都说德语,而且皇帝议事会、大部分领地和帝国城市都使用它。但需要注意的是,那时还没有统一的新高地德语。在帝国的南方半个疆域内,更多的是使用南德方言,这也是影响着公文体的语言;在萨克森、图林根、黑森和莱茵河中游地带,人们说的是中古德语;在北方,通行低地德语或弗里斯兰语。
毕兴在1789年还强调说,“一名德意志人常常听不懂另一名德意志人说的话”。帝国议事会给帝国西部的法语区书写公文时,大多使用当时在所有地区都通用的拉丁语。除了法语以外,在帝国的一些地区还使用意大利语、波兰语、捷克语及其他语言。毕兴于1789年写道:“斯拉夫语是德意志的第二大主要语言。”所有这些语言,至少在约瑟夫二世1780年执政以前,在他的世袭领地上没有系统地受到压制。
 ▲神圣罗马帝国平民油画形象
▲神圣罗马帝国平民油画形象
那时还没有采取词语德语化的措施,也很少禁止使用其他的语言,这些措施、禁令都是后来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普遍保存下来的东西。在这古老的帝国里,还没有形成给欧洲和世界带来那么多灾难的鲜明的现代民族主义。对帝国来说,那时西部使用的法语,是一种特别的补充和丰富,南部使用的意大利语和斯拉夫语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毕竟展现了古老帝国无所不包的特点。
参考资料:
Büsching,Erdbeschreibung,Bd.5,S.26.
Grellmann,Heinrich Moritz Gottlieb: Historischstatistisches Handbuch von Teutschland und den vorzüglichsten seiner besonderen Staaten. Gttingen 1801,S. 28.
Aretin,Karl Otmar von: Das Alte Reich 1648-1806,Bd. 1. Stuttgart 1993,S. 4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