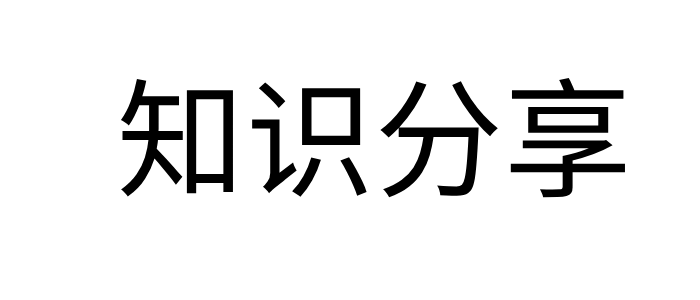原 下 的 日 子
文/陈
1
新世纪第一个农历新年过后,我买了20多袋无烟煤和粮食,回到农村老家的老房子里。
站在门口,我和送我回来的老婆女儿挥手告别,看着车绕着沟口破败的关帝庙转。
我折回大门,进入了那个隔一年才刚刚清理过落叶的小院。我觉得心里有点酸。我已经遇到一个60岁的老人了,何必回到这个近十年的空巢。
从窗框看去,一缕缕灰色的煤烟从铁烟囱里悠悠冒出,炉子正在把屋子里整个冬天积攒的寒气烘干。
从前院到小院,南窗前的丁香,东西栅栏下的三棵枣树苗,枝头未见动静。
然而,三五朵玫瑰的枝头上却绽放出紫色的小花蕾,这显然是春天的讯息。
但是整个小院太静太冷,还是让我难以转换回归乡村的喜悦。
我站在院子里,抽着雪茄。东边的房子几乎成了荒废的花园,兄弟俩都为了基建选了新房,搬出去住了很多年。
西街坊曾经是这个村有名的八院,挤得像鸡笼一样,都搬到村里新建的宅基地上定居了。
我家以前是我爸和两个表哥主导的《三国志》。全盛时期,祖孙三代有15、6个人从七八个或宽或窄的门口进进出出。
在我混乱的生活部分,我看着村民们把装着我奶奶和那个叫吴瑕的人的黑色棺材抬出来,然后用粗大的抬杆把他们绑在街门外。
在儿孙们的哭喊声中,他们抬出村子,抬上原来的土坡,沉入新挖的坟墓。
后来,我遵循这个大致相同的仪式,亲自处理我父亲和母亲从房子院子到墓地的最后验尸过程。
多少年来,无论事情有多重要,我都没有错过由堂兄弟管理的两个叔叔和一个阿姨最后离开家和村子,走进原坡一个角落的坟坑的过程。
现在,我的兄弟姐妹,堂兄妹,还有我的孩子,都陆续离开了这个家,或者在天空的一边,或者村子的另一个角落,过着自己的生活。
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站在祖屋的这个小院里,给我留下了拥挤热闹的印象。
一股冷风吹到了原来的斜坡上。以前从来没有空过。从来没有空摔。从来没有洞。
我脚下是我们祖先反复践踏的土地。现在我站在这个有着许多代人足迹的小院子里。
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要再回来,因为这已经是我行动前的决定了。
丰富的汉语中有一个词叫龌龊。一段时间以来,我充分体会到了这个词无穷无尽的内涵。
我听到炉子上的水壶发出噗噗的声音。我沏了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
我坐在坐了近20年的藤椅上,啜着香茶,看着灶膛里红红的木炭。
我的耳边仿佛萦绕着那些见过面甚至根本没见过面的祖先的声音:嘿!你早就应该回来了。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搞不清是被鸟叫声吵醒的,还是醒来时听到了鸟叫声。我第一反应是斑鸠。
这绝对是一大群鸟最单调平淡的叫声,但也是我生命磁带上最敏感的叫声。我赶紧穿上衣服,坐了起来。透过窗户望去,后屋的屋顶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
在清晨的寒风中,一只斑鸠围着另一只斑鸠打转,点头翘尾,发出持续的咕咕声和咕咕声。
哦!推动生命运动的春天的旋律,在还披着寒衣的斑鸠的躁动中传递。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泪模糊了。
2
傍晚,我走在巴河长长的河岸上。堤上有被雨雪浸泡成黑色的枯蒿草。沉到西苑坡顶的蛋黄般的太阳,软软的,弱弱的。
另一边,一片杨树林在蒙蒙的雾气中依然凛然肃穆。河水如此清澈,以至于不能用手阻挡。
一只雪白的鹤在我眼前从下游飘到了浅水区。
我偶然发现,在对岸的沙地上,一个人提着两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子,从一个巨大的碉堡里走出来,把笼子里的石头倒在石墩上,然后挑起一个空笼子走回低洼的碉堡。
有一个用三脚架支撑的铜丝篮筛。他把刨好的沙子和石头扔向芦苇筛,发出连续均匀的响声,石头和沙子在芦苇筛的两边分开。
我在河堤上站了很久,看着那个人走出碉堡,又回到碉堡。它离Xi安不到30公里。城市里的霓虹此刻应该是五彩缤纷的。
各种休闲娱乐场合开始进入精彩期。在暮色渐渐融合的沙滩上,那个人还在碉堡和石垛之间来回走着。这个人以这样的姿态存在于世界的这个角落。
我突然想到,印在画框里的稿纸,就像那个筐屏。他筛在篮子里的东西是一块一块的。我在“筐筛”上筛出的是一个正方形的汉字。
不管现在的稿酬标准是高是低,是贵是便宜,都一定是农人的石头没法比。
我意识到我还没有无聊到矫情的地步,但我更彻底地意识到了构成社会整体坐标的这一极:这一极与另一极的粗细强弱之差。
这是新世纪的第一次。
早春。这是我回到原下祖屋的第二天傍晚。这是我的家乡那条曾为无数诗家墨客提供柳枝,却总也寄托不尽情思离愁的灞河河滩。
此刻,三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的霓虹灯,与灞河两岸或大或小村庄里隐现的窗户亮光;豪华或普通轿车壅塞的街道,与田间小道上悠悠移动的架子车;
出入大饭店小酒吧的俊男靓女打蜡的头发涂红(或紫)的嘴唇,与拽着牛羊缰绳背着柴火的乡村男女;
全自动或半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与那个在沙坑在箩筛前挑战贫穷的男子……构成当代社会的大坐标。
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在这个坐标中找到了心理平衡的支点,也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3
村庄背靠白鹿原北坡。遍布原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阴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释的残雪下,
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茵陈,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卑称臭蒿子。
嫩黄淡绿的茵陈,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
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幻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
泡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暴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
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然后惊异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
小麦扬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
椿树的花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秀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里,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
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原坡和河川里的花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便一波迭过一波。
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原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
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
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神奇。
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
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
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
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
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几番浓霜击打,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
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仰起脸来,
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素净的田野。
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止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淡光色里走出门去,
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
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4
漫长的夏天。
夜幕迟迟降下来。我在小院里支开躺椅,一杯茶或一瓶啤酒,自然不可或缺一支烟。夜里依然有不泯的天光,也许是繁密的星星散发的。
白鹿原刀裁一样的平顶的轮廓,恰如一张简洁到只有深墨和淡墨的木刻画。
我索性关掉屋子里所有的电灯,感受天光和地脉的亲和,偶尔可以看到一缕鬼火飘飘忽忽掠过。
有细月或圆月的夜晚,那景象就迷人了。我坐在躺椅上,看圆圆的月亮浮到东原头上,然后渐渐升高,平静地一步一步向我面前移来。
幻如一个轻摇莲步的仙女,再一步一步向原坡的西部挪步,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屋脊背后。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
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哪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沛公军灞上”,灞上即指灞陵原。
汉文帝就葬在白鹿原北坡坡畔,距我的村子不过十六七里路。文帝陵史称灞陵,分明是依着灞水而命名。
这个地处长安东郊自周代就以白鹿得名的原,渐渐被“灞陵原”“灞陵”“灞上”取代了。
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灞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
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在风高月黑的那个恐怖之夜,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灞河,
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嘘出一口气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大唐诗人王昌龄,原为西安城里人,出道前隐居白鹿原上滋阳村,亦称芷阳村。
下原到灞河钓鱼,提镰在菜畦里割韭菜,与来访的文朋诗友饮酒赋诗,多以此原和原下南灞水为叙事抒情的背景。我曾查阅资料企图求证滋阳村村址,毫无踪影。
我在读到一本《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除了人皆共知的“年年柳色,
灞陵伤别”所指的灞桥,灞河这条水,白鹿(或灞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
任他朝市自营营。
独寻秋景城东去,
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诸多以此原和原下的灞水为题的诗作中的一首,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记的一首。
一目了然,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苟的龌龊惹烦了,闹得腻了,倒胃口了,想呕吐了,却终于说不出口呕不出喉,或许是不屑于说或吐,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还有什么龌龊能淹没脏污这个以白鹿命名的原呢,断定不会有。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自己烧水沏茶。把夫人在城里擀好切碎的面条煮熟。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
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一觉睡到自来醒。当然,每有一个短篇小说或一篇散文写成,
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是原下这两年的日子,是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
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摘自陈忠实《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
写作平台正在升级, 写作训练营正在进行中,详情阅读原文 | 关注公号 唐糖小君写作课 掌控平台新动态
友情链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