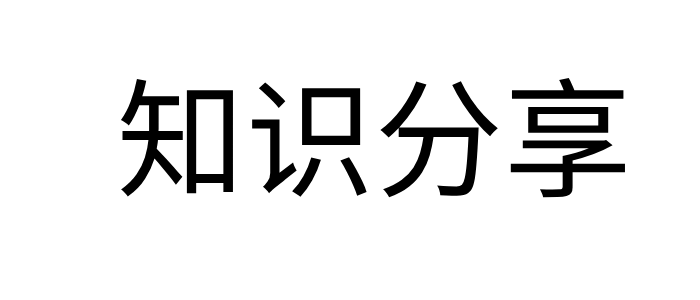长春宫西北墙上壁画《潇湘情缘》
长春宫西北墙上壁画《潇湘情缘》
文/商伟
在杨鹏的作品中,长春宫是华丽而梦幻的。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自1791年《红楼梦》活字版出版以来,以其为题材的各种绘画开始流行。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组《红楼梦》幅壁画出现在故宫的长春宫。上面这首诗描述了杨鹏观看宫中壁画的印象和情感:他倚着长春宫的雕花栅栏,在多通道的走廊里流连忘返,周围壁画上的“《红楼梦》里人”让他凝视着,若有所思。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却近在眼前,那么鲜活生动,却又像梦一样不真实,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又一次见证了“假的时候是真的,真的假的,没办法”的奇迹。
它是紫禁城西六宫之一的长春宫。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后宫嫔妃的私宅。其中,慈禧太后(1835 ~ 1908)是第一位。她在同治年间(1862 ~ 1875)一直住在这里,直到光绪十年(1884)移居储秀宫。
长春宫采用黄琉璃瓦歇山顶的建筑风格,有五个大殿。东侧大殿叫岁寿殿,西侧大殿叫城西殿。坐在正殿朝南的卧室里,正对着体元殿后面宝霞的一个室外戏台,中间是一个宽敞的庭院。庭院四周是游廊,游廊与寺庙相连。院子的每个角落都有转角回廊,回廊的左右墙壁上,有18幅《红楼梦》的巨幅壁画,和墙壁一样高,宽度不一!
普遍的看法是,这组壁画与慈禧有关。她是《红楼梦》的忠实读者和铁杆粉丝。她曾经从民间拿《红楼梦》幅画,让我把写诗当儿戏,她一直把自己当贾母。许多学者认为,这组《红楼梦》幅壁画是1884年绘制的。那一年恰逢慈禧50大寿。在长春宫的室外舞台上,在宁寿宫和慈宁宫的室内剧场里,举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歌剧表演,从10月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20日。壁画也是庆生的内容之一,所以画面上经常可以看到庆生的题字。舞台上的表演配合墙上的壁画。一方面,长春宫被建成了一个表演空间;另一方面,大观园的彩绘景色尽收眼底,犹如舞台的延伸布景,永久上演一幕幕《红楼梦》的经典场景。这样算下来,这组壁画已经有135年的历史了。
由于历史久远,风吹日晒,气候干燥等因素的影响,壁画的颜色不再像以前那样鲜艳,细节也越来越模糊,局部外观出现龟裂的迹象。为了保护壁画,在20世纪90年代为它们安装了玻璃罩。但壁画的宽阔格局和恢弘大气仍依稀可辨。这组壁画集中表现了《红楼梦》的大观园景观,尤其是外景,多为采诗宴饮的场景。场景多在中远程,场景广而深远,人物众多,细节丰富。周、徐秉斌、等都对壁画内容进行了考证。其中如《湘云醉眠》、《文清撕扇》、《宝钗蝴蝶》都是《红楼梦》画插画的保留节目。如今的“贾母园”画面,表面上已经开裂、破损严重,但贾母坐走椅游览大观园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令人想起清宫内外流行的“边走边玩图”。《梦游乌托邦》出自小说第五回。图中一仙女捧尘,引宝玉。楼上那个女的在唱《红楼梦》。它是一座园亭,有着极目远眺的幻境,投射出人间大观园的景观。
在我看来,在长春宫《红楼梦》幅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幅,分别绘在正殿游廊东西两端的墙壁上。从主厅的卧室出来,看着
但有趣的是,在长春宫的18幅壁画中,正是这两幅,情节最薄弱,场景最难辨认。其中东北角东墙的一幅,徐秉斌暂定名为“金兰宝钗”,或为黛玉与宝钗在游廊相见交谈的情景。西北角西墙的那幅只能叫《潇湘情缘》,描写宝玉逛潇湘馆,看见黛玉在长廊上走在前头。这种场景在小说中似乎没有出处,在现存的《红楼梦》张图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莫名其妙。
不过,这两幅壁画在《红楼梦》年是否有依据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兴趣,他们在经营空间的错觉,制造观众的错觉:他们把正厅前的走廊延长,画进墙上的绘画空间,也就是大观园的梦幻世界,故事场景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
 壁画《贾母花园》栩栩如生。
壁画《贾母花园》栩栩如生。
为了突出大观园的主题,两幅壁画都是用错觉画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潇湘情缘》的画面:画面上一条画过的走廊,它的左侧向画外的空间敞开,在走廊的尽头向左拐,好像还有一个山洞;是右边的墙,上面有两个装饰性的通透窗户。画家刻意通过走廊来管理画面空间的深度,将我们的目光引向走廊尽头的木隔断。隔墙两侧门柱上各有一副对联,梁上匾额写着“月动竹影”。门框外,是室外花园。透过狭窄的阳台望去,我感到眼前一亮。满眼绿色中有竹丛,其中一块太湖石立于石基上,地面用石板、鹅卵石铺成花纹。
作为观众,我们的位置对于观看这幅壁画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正站在长春宫正殿游廊的尽头和3354处墙上彩绘游廊的起点的真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交汇处。我们从主厅前的走廊一路走下来。面对壁画,我们看到一个女人沿着画中的画廊向我们走来,但此刻,她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因此
,她迟疑,伫足,半侧过身去张望。果然,顺着她搜寻的目光看去,在她身后长廊的尽头,贾宝玉从右边墙壁的最后那个立柱的后面探出头来,仿佛正凝视着这位女子,同时也面向我们,形成了一次目光对视。这是错觉画常用的把戏,令知情者会心一笑:画中人朝向观众,并与之对视,正是一个邀请入画的姿态,而观众必须穿过画中的长廊才能抵达他的所在。这幅壁画的用意也正在于此:它引诱我们顺着长廊走进图画,与宝玉相会。可是我们心下明白,一旦接受邀请,哪怕沿着长廊往前多走两步,我们就会像《聊斋志异》中梦想穿墙而过的崂山道士那样,“头触硬壁,蓦然而踣”。
这条走廊的另一头,也就是长春宫的东北角,迎面看去,也有一幅类似的壁画,即暂定为“金兰黛钗”那一幅。它以同样的方式,将正殿前面的游廊整合进图绘幻象之中。图上两女子在廊中相见,左侧壁上有透窗,可见户外风景。走廊的尽头也有一副对联:“庭小有竹春长在,山静无人水自流。”其上的扇面式匾额书“绿竹长春”四字,暗含长春宫名。其下是半开的屏门,左右两扇门面上各书“延年”“益寿”,显然是为了配合慈禧祝寿的场合。门上的墙面有瓦制的古钱纹装饰,门外竹影婆娑,与透窗所见的风景连成一片。
从内容和构图来看,这两幅壁画是否别有寓意?不难看出,这两幅壁画巧妙地利用了画面与周围建筑实体的关系,将长春宫正殿前的长廊打造成通向大观园的过道。它们分别设置在了正殿游廊的东西两端,造成了游廊朝两个相反方向直线伸进的错觉,从而无中生有地拓展出一个神秘而梦幻的虚拟空间。“金兰黛钗”中背对观众的女子,将目光引向屏门之外的园林,“潇湘幽情”中的女子回身侧转,也对长廊尽头的那座室外花园流连反顾。与狭长幽暗的长廊形成对照,那里春光明丽,院空人静,好梦初长。这一设计独具匠心,却不露痕迹,令人在踟蹰彷徨之际,心生恍惚:莫非这就是大观园的通道,引向《红楼梦》中那个盛筵常在、青春永驻的世界?
这两幅壁画不仅通过图绘长廊的无缝对接,制造了从长春宫走进大观园的幻象,而且将长春宫延伸进了画面上的大观园,也就是把长春宫的屏门、门框、长廊、廊柱等建筑实体,都绘入了大观园的虚拟空间。其结果是抹去图画与建筑、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在封闭的长春宫内营造出大观园室外风光的瞬时幻觉。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图画内外的廊柱和柱础一一对应,从样式到色彩,都没有明显差异。在长廊东西两头的这两幅壁画中,可见两处屏门,“金兰黛钗”中的一处在长廊的尽头,“潇湘幽情”中的另一处画在图中的右壁上,其中左扇门上隐约可见一“祥”字。而这两个图绘之门实际上都照搬了长春宫的屏门。我们只要从这两幅壁画前后退几步,就可以看到正殿游廊左右两边的墙上,都各有一道绿色屏门。随着墙面延伸进画面,真门随即被假门所替代。长春宫与壁画大观园,原本一真一假,泾渭分明,而且互不相关,可是经过错觉壁画的处理,就变得真假难辨了——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造成了真假交错的视幻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画上的屏门和廊柱均为绿色,与图绘大观园中绿竹葱葱的基调完全一致。慈禧酷爱竹子,壁画上的匾题“绿竹长春”印证了她祈求长生不死、青春永驻的愿望,同时呼应了祝寿的场合与主题。由此或可推断,如今长春宫廊柱的朱红色是后来刷上的,当年原本为绿色,这两幅图画中的长廊和竹丛可以为证。我们知道,确保图画与周围建筑之间的连续性,正是这两幅错觉壁画总体设计的基本逻辑:把长春宫投射进大观园,也就是将长春宫变成大观园的镜像。在长春宫内起居漫步,已恍若置身于风光旖旎的大观园了。
长春宫的《红楼梦》壁画对于我们理解《红楼梦》和清代宫廷的视觉艺术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错觉画曾一度盛行于雍正、乾隆时期的宫廷中,通常采用贴落的样式,也就是将图像画在小块的绢帛或其他质料上,然后贴在板壁上,形成一幅完整的大幅作品。长春宫的《红楼梦》图画使用了壁画的形式,而且不再出自宫廷画师之手。根据王仲杰的说法,这组壁画是由清廷营造司的彩画师陈二与坊间画铺的画师古彩堂合作绘制而成的。但他们无疑以壁画这一新的形式延续了宫廷错觉画的传统,并向它致意。
更重要的是,曹雪芹本人就生活在宫廷错觉画的黄金时代,并从中汲取了小说写作的灵感与资源。在他笔下的大观园化作长春宫壁上真幻莫辨的图画影像之前,曹雪芹早已把错觉画写进了自己的小说。《红楼梦》第41回写刘姥姥在怡红院迎面看见壁板上的画中女孩儿,却误以为是真人,上前去拉她的手,结果把头撞得生疼——那正是贴落画在《红楼梦》中的刹那闪现。而长春宫的这幅壁画引诱我们顺游廊破壁而入,与宝玉画中相会,也正是错觉画的故技重施,令人会心莞尔:我们发现自己被放在刘姥姥的位置上,一时重温了与错觉画相遇的迷惑瞬间和喜剧场面。
作为一部小说,《红楼梦》从一开始就着迷并得益于清宫错觉绘画的“造假”艺术,在以文字呈现大观园时,营造了千变万化的视幻效果。而这样一部小说最终又以错觉壁画的形式,进入紫禁城,成全了《红楼梦》与清代宫廷视觉艺术的一段夙世因缘。在长春宫的这两幅壁画中,画师向曹雪芹致敬,并对他的小说及其对错觉画的呈现,做出了一个不乏机趣的评论。这两幅作品因此具有了“后设绘画”(Meta-picture)的特征。它们既是关于小说的绘画,又是关于绘画的绘画,也就是以错觉画的形式对错觉画自身做出了评论。
总之,长春宫的巨型壁画不仅以《红楼梦》为题材,还通过一个回顾的姿态,为《红楼梦》与清宫视觉艺术的渊源关系,提供了一次历史见证,同时也为《红楼梦》的大观园迷宫之旅,指示了一条门径。我们无妨由此出发,去观览文字造就的大观园,去领略《红楼梦》小说叙述艺术的视觉性,及其18世纪的时代色彩。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支持和张淑娴研究员的多方协助,《红楼梦》壁画照片由古建部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