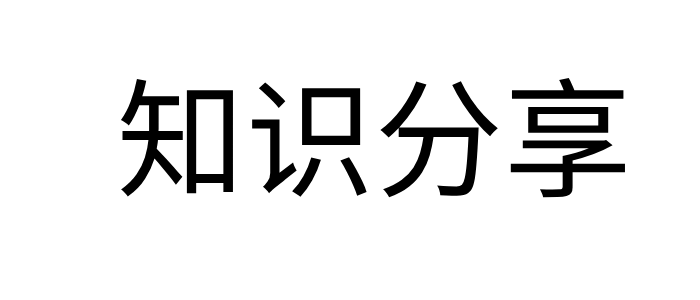虚拟主播直播2小时收入达百万
代表网络的,有红人,有以前的真实主播,有今天的虚拟主播。
最近,虚拟主播Shoto在哔哩哔哩所有电视台中排名第一,在两个小时的直播中赚了超过一百万美元。此消息一出,一举冲上微博热搜,引发不小争议。

“我看不懂枪套……”
“直播不是一种陪伴吗?有粉丝愿意消费内容,喜欢内容不是很好吗?”
在沸腾的舆论场上,围观者的讨论声一会比一会高,有人不理解,有人一直坚持为爱发声。当然这种噪音也是从侧面说明的。如今走进直播间的虚拟人物,已经开始打破圈子,闯入大众视野。
在说虚拟主播的火爆之前,先说一下数字虚拟人。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外形数字化的虚拟人物,在外貌、举止甚至思想上与人类相似,通常依赖显示设备存在。著名的虚拟人物有、刘、阿亚依等。

(左为,右为刘)
虚拟主播是借用虚拟角色,向各种视频网站和社交平台投稿的主播,其中以虚拟的YouTuber最为知名。其核心功能是替代人工服务,完成视频内容制作和一些简单工作,降低服务业成本。
虚拟人逐渐火热,但并不是这几年才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超人气动画《超时空要塞》的女主角林明美就以演唱主题曲《可曾记得爱》开启了虚拟偶像时代。
2007年,世界第一公主初音未来公主殿下以33,360,010-30,000的魔力一炮而红,再次掀起了一波虚拟偶像的热潮。
2013年,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我和虚拟的邓丽君一起唱歌,这让观众感到惊讶,也让虚拟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2016年,日本“绊爱”诞生,开创了“虚拟主播”的概念。自绊爱流行以来,2017年出现了大量虚拟YouTuber,虚拟主播经历了爆发式增长。

目前,各平台的虚拟主播大致两种类型:纯AI类、真人驱动类.前者最大的特点是可以24小时直播,成本低廉,有效降低了品牌对人力的依赖。
但其交互性较弱。对于观众的提问和诉求,它只能机械地回答预设的答案,导单能力远不如直播主播,用户体验较差。
后者是由“虚拟形象”和幕后“中之人”组合完成.《中间人》drive由动作捕捉技术驱动,将真人的动作同步到虚拟人物身上,从而达到实时互动的效果。

真人驱动的虚拟主播几乎完美解决了互动问题,用户体验普遍较高,但其技术门槛和相应成本也较高。
为了让这两个虚拟主播的优势互补,现在采用“真虚拟人”的组合模式,虚拟人往往自带流量,知名度高,可以形成一定的号召力,大大提升直播效果。

大厂争相入局
虚拟主播之风吹来,敏锐的互联网厂商已经听到了风声。
腾讯、网易、B站、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都纷纷入局虚拟数字行业.晨星、CICC、建银国际等知名投资机构也在这条赛道投入巨资。据统计,仅2021年,虚拟数字人赛道就发生了近20起融资事件,金额超过20亿元。
2021年10月,自称能“捉妖”的虚拟美女专家刘在上线。刘发布的第一个视频就获得了300多万个赞,短时间内上涨了百万,被称为2021年现象级虚拟人。

同年年底,百度推出首个可以在手机APP上与用户互动的明星数字人,公众可以与之进行语音对话。不久之后,字节跳动独家投资了虚拟IP形象“李维客”。
不仅如此,在天猫商城、淘宝等平台上的美妆店,还打造了虚拟导购AI Wendy,为消费者推荐合适的口红。
其实,资本对于虚拟数字人的青睐一直都在,此番包括互联网大厂在内的众多企业,纷纷涌入虚拟数字的赛道,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
近两年,“元宇宙”概念爆火,各家企业都想以不同的形式贴近元宇宙,为自家注入新活力,而虚拟人物正是一个切入点。而且,无论是虚拟歌手还是虚拟主播,都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新事物,开发虚拟数字人物能进一步拉近彼此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自“绊爱”诞生以来,虚拟主播行业展现出了不俗的吸金能力。日本虚拟主播第一企业“彩虹社”,就在短短5年内营收翻了500倍。如此可观的收益能力,自然也会吸引资本投入。
除了互联网大厂,传统线下企业也力图打破“次元壁”,尝试与年轻消费者进行对话,在新领域有所建树。

今年1月,美的旗下品牌华凌宣布,两位虚拟偶像正式入职成为其数字化新员工,分别担任数智体验主理人和潮流设计主理人。
无独有偶,2021年万科总部优秀新人奖的获得者“崔筱盼”,也是一位数字员工。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入场,在资本的加持下,“虚拟人”的相关产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和高峰。

虚拟主播是下一个直播风口?
在国外,虚拟主播活跃于YouTube;而在国内,B站是虚拟主播的一大聚集地。
2021年,B站CEO陈睿在周年庆上表示,过去一年共有超32000名的虚拟主播在B站开播,同比增长40%,虚拟主播已成为B站直播领域增长最快的品类。
从B站虚拟人直播数据看,虚拟主播投稿量达到189万,同比增长50%;虚拟主播稿件播放量达83亿,同比增长70%,直播弹幕互动量达5.6亿,同比增长100%。
依照2021年的市场状况来看,今年可能会迎来虚拟主播的爆发性增长,虚拟主播依然会是直播行业的一个趋势。
然而,正如其他新起的行业一样,虚拟直播也存在着很多的障碍。
一方面,从长期来看,虚拟主播的成本低于真人主播,但其转化效果远不如真人主播,很多虚拟主播只是机械化地读产品卖点,神情动作都很有限,无法良好引导用户下单。
纯AI类的虚拟主播,造价便宜,可以在系统里自选开播形象,一个月花费几百到上千元。但这类机械的主播主要用来填补真人没有开播的时间端,比如凌晨档、春节期间,或者作为录播,应用在产品介绍中。
而更为灵活机动的真人驱动类虚拟主播,往往价格昂贵,仅仅是其中的三维虚拟形象技术成本就达几万到几十万。
除了技术成本,还有团队、设备成本,每一项技术开发都在加大成本、压缩利润空间。不仅如此,真人驱动也存在管理风险。
诸如,与高级的场景打造相比,中之人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作为整个环节中价值最低的人,很有可能因为无法得到相应收入或回报而出走。而“中之人”是角色表现的一大灵魂,如果更换可能会遭到粉丝反感,甚至脱粉。
另一方面,在明星塌房现象屡见不鲜的情况下,一直主打“人设永不崩塌”的虚拟人戳中人心,很多人将虚拟主播视作真人明星的“替代品”。
然而,实际情况是虚拟人可能不会塌房,但会休眠。今年5月,国内顶流虚拟偶像团体A-Soul组合成员珈乐,宣布进入“直播休眠”状态,这是V圈给自己的一记响亮耳光。

除了打脸,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未来的虚拟主播也很有可能面临同样的遭遇,让粉丝在感情投入上多了一分谨慎。
总的说来,虚拟主播产业还处在发展初期,还有很多挑战需要一个个攻克。随着未来技术的迭代更新,其发展空间还非常大。
作者丨顾影